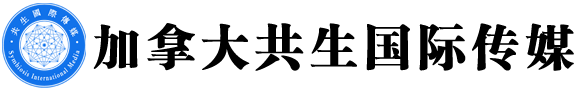细雨菲菲的早晨,大巴拐入海宁的袁花镇,缓缓穿行于狭窄的村道上。房前屋后,皆为见缝插针式的农作物。低矮的稻穗已发黄,沉甸甸垂着头,依傍着田埂上的几株玉蜀黍。棚架下吊着细长的丝瓜、翠绿的豇豆,还夹杂着一些叫不出名的蔬果。
大巴停下,迎面出现一堵高大的粉墙,便是金庸故居了。迈入静谧的大堂,抬头见到高悬的牌匾,上书斗大的黑字:进士、文魁。令人惊讶的是故居的格局。三进老宅皆为横向宽阔,悠长一排,与北方常见的竖向进深大宅子截然不同。同样的横向长排,以前只在北京恭王府的最后一进见到过。此种格局,气势如虹,无怪孕育了文坛一代天骄。
远处传来朋友们的嬉笑声,大家勾肩搭背,热闹地合影。我独自一人,沿着一条幽暗的甬道迈入了萧疏的后园。靠墙根处,有两株树。一株是桂树,花期已过,不再飘香,另一株,却是北方常见的枣树,枝头累累,挂满金红色的果实,分外诱人。我站在树下,仰望着头顶一粒粒饱满的枣子,遥想93岁高龄的大师,可曾在港岛灯火阑珊之夜,怀念过故乡后园秋日的红枣?
步出大门,忽见一戴眼镜的中年男子,擎一柄黑布油伞,沿着影壁匆匆走过,口中还喃喃自语:“嗯,还真有人来呢。”声音中透着不难察觉的欣慰。
大巴启动了,轻轻拂过桑林里茂密的枝条。远处,那扇黑漆大门徐徐关闭了。导游说,两个月来,我们是首批来访者。
袁花村不收门票,也没有热闹的旅游商品售卖,我却独爱他门前那份寂寥。想起方才来的路上,跨越杭州湾的彩虹桥时,少君曾向我解释为何海水会是混浊的黄色。他赞叹,污泥浊水养育的鱼虾味道才鲜美,并提醒我,水至清则无鱼。
我未做声。究竟是在喧嚣热闹的污泥浊水中蜕变为一道肥美的菜肴呢?还是在碧波清流中安详自在地独往独来呢?怕也是见仁见智的选择吧。好在上帝是公平的。至清还是至浊,都仅有一次生命。
踏入乌镇弯弯曲曲的石板小巷,立即爱上了它的古朴。问路旁站着的几个婆婆,小镇人何以这般明智,竟耐得住寂寞、抵御了诱惑,未卷入拆房盖楼的商业大潮?婆婆们面露得意之色:“我们穷啊,盖不起新房嘛!30年风水轮流转哦。”
导游心地善良,总要挑选当地最干净体面的饭铺招待大家用餐。众人快乐地享受着轮番上桌的鸡鸭鱼肉。我却悄悄渴望着,若能品尝街边小摊上那些各具特色的地方小吃该有多好。
春天带领加拿大教育家来华交流时,也曾遇同样情形。祖国人民好客,总爱用品种丰富的炒菜来表达对客人的尊重。京城四日,顿顿七碟八碗,到了最后一天,即便对中国美食倍感新鲜的老外们也难免倦怠,桌上剩下整盘整盘的菜肴,令人心疼。最后一天中午,我自作主张,把众人引入雍和宫大街边一家饺子馆里。店面狭窄拥挤却座无虚席。我点了6种不同馅的水饺,又叫了四碟凉菜,小葱拌豆腐、黄瓜木耳、金针菇等,结果大家一扫而光还意犹未尽。
乌镇的溪边,竹编的蒸笼敞开了盖子,只见一坨坨色泽暗绿的青团,看去颇为神秘诱人。我刚开口询问,“秋天既无麦苗,也无嫩蒿,拿什么东西染成绿色呢?”一位作家在旁急扯我衣袖,于是,在豆腐西施的白眼下匆匆离去,终是无缘。
小巷两旁,一家接一家,摆满了烘烤霉干菜饼的炉灶,摆在铜盆里煮熟的大芋头似乎还冒着热气。见我围着炉灶,探头细看那些一寸大小的霉干菜小饼,旅美作家少君二话不说,掏钱买一袋分给众人尝了。
茅盾故居听说5点就要打烊,于是甩开在“木心故居”里流连忘返的大队人马,踏着石板匆匆赶路。进得二门,尚未站稳,耳畔忽然传来细若游丝的柔声。四下里寻觅,便在天井那片低矮的兰草丛中看见了它。纤巧的身躯,灵秀的五官,灰黄夹杂的花纹招人怜爱。微弱的天光中,它仰头看我,又一声清晰的低唤。
抬首望去,高堂门楣半开处,大师的半身塑像隐隐可见,却已罩在苍茫中,面目模糊不清了。
正欲迈入展室,小猫竟再次发出呼唤。转身看时,它的目光依旧定定地瞧着我,分明有无限期盼。于是问站在游廊下闲聊的几个保安:“这可是无人照管的野猫?它是饿了吗?为何总盯着我叫唤?”
保安咧了嘴讪笑:“是哩,那野猫和你有缘,带上它走吧。”
踌躇之中,脑中却悄然闪出一句话。方才在小巷另一头长满青苔的“木心故居”里,满墙满壁都是名言,却仅有一句话进入了我的眼帘:“自作多情和自作无情,都是可笑的。”
心中似乎悟到了什么。在悄然降临的暮色中,我拔脚离去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END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点击图片,了解详情






欢迎关注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网站

欢迎关注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微信公众号
欢迎惠顾广告!联系方式:电话 胡宪 514-246-3958,胡海 010-15901065716